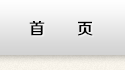震泽,与我的故乡盛泽是近邻。五十年代,盛泽到震泽,也要半天的水路。童年时,我住在盛泽镇上,因为交通的缘故,竟然没有到过震泽。后来,跟随父亲移居常熟,从父亲的嘴里,经常听说震泽的故事。
1947年至1949年,父亲一直担任地下党交通员,他负责从盛泽到湖州南浔一线的情报传递。交通员的工作是昼伏夜出,迈开双腿潜入暗夜,专门行走于田埂荒郊。他晚上从盛泽出发,半夜时分到达震泽,悄悄寻到市梢头的米行,找到同乡歇脚处,交换了情报,再连夜往南浔而去。有一次,发生了意外事件。父亲从南浔带了两支全新的德造二十响驳壳枪,要转交给吴江的地下党。他扮成捉蛇叫化子,将沉重的枪支用油纸包好,塞在破旧的提篮里。到震泽,也是半夜,露湿雾重,又饥又饿。因为带了枪,不敢在同乡处休息,便寻了个野坟地里的柏树下打盹。朦胧中觉得天色初晓,远处传来人声喧哗,父亲大吃一惊,以为是敌人搜捕来了,便赶紧在田野里狂奔,寻了个土坟堆,将两支枪塞了进去,还差点给盘在草丛里的火赤链蛇咬了。他急步回到震泽,躲在同乡的米行里,提心吊胆的藏匿了一整天。到了夜半,他再去寻枪,哪里再寻得到那个野坟地?乡村的土坟暗夜里根本无法辨别,父亲只记得这个土坟在震泽与坛丘之间,久久搜索无果,白天又不能耽搁,只得颓丧而回。这件事,一直挂在父亲心上,解放后“肃反”时,还牵了他头皮,写了几十页检查。
不过,父亲跑夜路的本领就是在那三年里练出来的。1970年,他在虞山尚湖的五七干校劳动,半夜里给稻田放水,狭长的田埂,伸手不见五指,他仍走得飞快,同行人在后面连喊“老俞,慢点”,他却已经没了踪影。父亲骄傲地对我说,他一夜天可以从盛泽到震泽,走个来回。
应荆歌之邀,我来到了久违的震泽。登上禹迹桥,与慈云塔比肩,我就有一种梦中依稀相识的感觉,那种江南小儿女的情怀,在水清风爽的小巷中,悄悄地剪裁着甜情蜜意。走进宝塔街,高高的女儿墙,宽宽的石板路,横跨街楼的砖雕门楣,老式米行的眉毛天井,就仿佛回到了我童年时代的盛泽茶叶弄。口角生香的熏青豆茶,还津津留味,那多收了一斗二斗三五斗的米行,也许,就是我父亲的避难所。走到丝绵作坊前,我抬头一看,楼窗下挂着三四串黑亮的酱肉,觉得象久违的老朋友一般亲近。酱肉、酱鸭、酱茴蛋,是吴江人的最爱,是一种久远的滋养,一直深入到我的骨髓,它是我生命里的维生素。记得1962年大饥荒,我从常熟逃到盛泽,奶奶从厨房里切了几片黑黝黝的酱肉,放在我的饭碗里,还有一只酱茴蛋,我狼吞虎咽,噎得咽不下去了。奶奶疼爱地说:“慢点吃,慢点吃。”我怎会慢点吃呢?我怕吃慢了,就会没得吃了。要知道,当时8岁的我,在常熟总是吃不饱,肚里几个月不见荤腥,麦片粥和糠饼,已经是城里有户口人的享有了。于是,在奶奶家里吃到的那一顿美食,成为我懂事后的第一顿美味。你说,我看到震泽宝塔街上的酱肉,能不象见到亲人一般的依恋吗?它救过我的命,它是我的救世主啊!
进师俭堂,过轿厅,转天井,上小姐楼,推窗临街,象回到了儿时童嬉的老墙门。我住过的茶叶弄里,也是这样一种格局的老房子,当然没有师俭堂这样气派这样进深,它只有二进,高高的女儿墙上有八角形的漏窗,楼梯上方也有翻转的隔门。旧时代,富裕的江南小镇,常是兵匪盗贼经常光顾的地方。要想数百年保存完好一处大宅院,真是凤毛麟角。震泽师俭堂,就是这样一处宏富精美、深达六进的豪宅。我每到一处这种富有含光韬晦之美的宅园,总会作一番悠远的遐想,想象它落成之时挥金如土的豪爽,想象它大家闺秀或是小家碧玉式的吞吐能量。宅第就是一种强大的气场,气场的中心就是人的生命,以及人的灵魂和它情不自禁的舞动。
遥想当年情景,师俭堂初露峥嵘,满城乡亲争睹门楼风韵。轿厅里,秀才的青布小轿,官员的八抬大轿,小姐的锦幛帷幕,新娘子的流苏凤冠,一时间,莺莺燕燕,蜂蜂蝶蝶,祝贺颂歌与慈云塔影齐名;红男绿女与丝弦喜乐共进,谁能不说,这是震泽志书青史留存的建筑佳话?谁能不提,清清荻河漫不经心吐出一串珍珠?我总是在它的楼台上寻觅旧痕,那磨得锃亮的铜环,那走得滑溜的步槛,那彩色的西洋玻璃窗,无数个月明月晦之夜,伴随着老宅这个迟暮的美人,悄悄停停地传递着有关风月无关痛痒的信息。
历史也有会心的一笑。大宅院的旧主人会老去,大宅院的新子孙会远走。于是,七十二家房客挤进了老宅院,三分明月自然会被切割成柴米油盐的算计。人生的故事也许会更多更细致,也许,曾发生过,男欢女爱,跳河投环:夜半歌声,鬼影出巡。远走的痛揉捻着远走的风,潜藏于永不停歇的欲望之河。
如今,师俭堂已成为震泽旅游的一张名片,一部无语的百年沧桑的纪录片。每到黄昏闭馆时,我依稀看到,昔日盛装演出的美人,挥洒着胭脂红的水袖,向游人作最后的谢幕,她的鹅蛋脸上,分明留着泪痕。她要卸妆去了,她要月下吟诗去了,她的纤纤素手,要轻轻拨动那永世的凤尾琴了。
告别师俭堂,风是新鲜的,水是清冽的。我站在禹迹桥下,迎着冬日午后的阳光,看到粮库老码头下,宽达数十米的石级没入荻河,七八个姑娘少妇正在洗衣,棒槌溅着水珠起落,一派恬静景象。这是震泽人的福分,与那熏青豆茶,与那黑豆腐干,一齐收入我的行囊。
俞小红(作者简介: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常熟市作家协会主席)